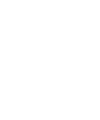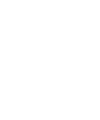我的仇敌成了我的道侣 - 第644章 送命题(加更四合一)
第644章 送命题(加更四合一)
陈易回到院落,推开门,隨手將提灯掛在门廊下,昏黄的光晕在风中摇曳。
“唉·—..—.”
一声幽幽的嘆息毫无预兆地在身后响起。
陈易脚步未停,径直走到院中的石桌前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冷茶,对於东宫若疏这种神出鬼没的出场方式,他早已麻木,甚至懒得回头看一眼。
东宫若疏很可惜他没有看到自己嫵媚的眼神,旋即一想,她已足够嫵媚了,
错显然不在她自己。
“那池子真有用么?”东宫若疏从阴影里飘了出来,绕著石桌转圈,好奇道“我许那么大的秘密,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她停在陈易面前,凑近了仔仔细细观察他的眼睛,仿佛想找出一点点蛛丝马跡。
陈易慢条斯理地啜了口冷茶,抬眼道:“没有。”
东宫若疏的肩膀彻底查拉下去,飘到他对面的石凳上,显得很沮丧。
陈易看著她这副模样,心中竟也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庆幸,旋即又化作更深的疑惑。
这笨姑娘·许愿时的动静那么大,池水翻涌符文闪烁,儼然非同小可,为何对这个“勾引”的愿望毫无反应?是愿望本身的问题?抑或是说,已经生效,
只是他们不知?
种种思绪浮过脑海,对於这笨姑娘,陈易虽有欲望,却始终没有多少情丝可言,她太大智若愚了点,若是真有了关係,为此负责,倒也无可无不可,偏偏东宫若疏是个魂、成了鬼,连那点可能性都抹去了。
“东宫姑娘,”陈易放下茶杯,略一作想道:“你执著於勾引我,除了回报太后之情,是否——也有你自己的私心?”
笨姑娘要是否认,他也就顺利推舟拒绝了。
东宫若疏闻言,抬起头,那双清澈的大眼晴里迷茫了一瞬,隨即坦荡地点了点头:“有啊!”
陈易眨了眨眼,眉峰微挑,“哦?什么私心?”
“因为很有意思。”东宫若疏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之前的泪丧一扫而空,“你不觉得吗?你跟襄王女很有意思,跟景王女也很有意思,跟好多女人都很有意思。”
听闻此言,陈易一时无言以对,准备好的话语都止住喉咙,他著实跟不上她的思路,也不知如何回答。
“这世上好像没有你得不到的女人,所以我想啊,要是你被我勾引了,会不会更有意思。”东宫姑娘理所当然道。
陈易看著她那副天真又执的模样,心中那点无奈忽然掺杂了一丝难以言喻的衝动。
他身体微微前倾,带著一丝若有似无的危险气息,缓缓问道:
“东宫姑娘,倘若—我是说倘若—倘若我真被你勾引到了,想跟你——假戏真做呢?”
笨姑娘的眼晴瞪大了一下,卡壳了一瞬。
“假戏——真做?”她重复著这四个字,清澈的眸子里充满了茫然和一丝—..—不知所措?
“不错,要知道哪怕你是魂魄,殷惟郢那里也有神魂交融之法,假戏真作倒也並不难。”
她歪著头,认真地思考了好一会儿,“那我再拒绝你咯。”
“若是你没得拒绝呢?”
东宫姑娘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东宫姑娘,你不怕我来真的?”
好一会后,东宫姑娘认认真真道:“不怕,我有师傅的剑意在身,就在魂魄里。”
陈易敛了下眸子,道:“那你成婚时怎么不用?”
“当时我怕一剑劈死你,现在不怕啦,现在只能劈伤你。”
陈易听了一时无话,倒是很想治一治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笨姑娘,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笨姑娘如今成了魂魄,偏偏他术法不济,对付魂魄的伎俩都没几个。
要是她有肉身,看看密瓜籽就足以让她打退堂鼓了。
跟这笨姑娘较真,简直是自己找不痛快。
“洗洗就睡了,別烦我。”
说罢,他起身,看也不看还飘在石凳上东宫若疏,径直走向屋內。
一番简单的梳洗,冰冷的水似乎浇熄了些许心头的躁鬱,但不知怎么,身体深处因那笨姑娘一番话语,一丝无名火略微点起。陈易和衣躺下,闭上眼,將这些心绪一一驱逐出脑海。
疲惫和心累终究占了上风,没过多久,陈易的呼吸变得均匀绵长,陷入了沉睡。
月光透过窗根,在地上投下清冷的光斑。
屋內一片寂静。
忽然,一道半透明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阴影里飘了出来,等候许久的东宫若疏悬浮在床边,好奇地打量著熟睡中的陈易。
他眉头微,即使在睡梦中,瞧上去也生人勿近。
但是,
“他是傲娇啊—”
从前听不明白,现在东宫若疏明白“傲娇”是什么意思了一一明明嘴上冷言相待,可还是给她准备了夜宵。
嘴是冷的,阳气是热的。
东宫姑娘的目光,不由自主地下移。
陈易穿著宽鬆的寢裤.—
她已许久未吃过阳气,现在有些目露精光。
笨姑娘抹了抹根本不存在的口水。
然后,她微微张开了嘴——.—·
陈易肉眼可见地打了个小哆嗦,睡梦中皱了皱眉,仍旧睡得沉沉。
毕竟笨姑娘哪有敌意,她只是想吃宵夜而已。
东宫若疏见他继续睡著,不想把他给吵醒,好一会后,才再次俯身,大口大口地吸了起来。
呼—一吸一呼—一吸-
?
寂静的房间里,只有陈易均匀的呼吸声,以及某只女鬼努力“进食”时微不可查的吸气声。
两日后,歇马坪,赌坊。
熟悉的喧囂、汗臭与来往侍女的浓香混杂在一起,管事劈里啪啦地拨打算盘,谋算著自己这月的分成。
陈易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算盘声为之一滯,管事侧目间带著一丝惊疑不定,而那人理会管事,径直走向最深处的雅间,推门而入。
岩坎正叼著水烟筒,眯著眼盘算,闻声抬头,当看清来人时,他脸上的慵懒瞬间凝固,瞳孔收缩了一下,手中的水烟筒都忘了吸。
—活著回来了?
“哟?陈陈兄弟?”岩坎放下水烟筒,堆起笑容,但眼底的惊疑挥之不去,“真是稀客!老哥还以为你-呢,就此一刀两断了呢?快坐快坐!”
陈易没坐,只是站在门口,脸色比离开时更显阴沉疲惫,衣袍下摆似乎还沾著未洗净的暗色污渍。
他扯了扯嘴角道:“托岩坎老板的福,差点就真『一刀两断』了。给你运点土货,差点把命给运没了。”
“这话怎么说的?”岩坎故作惊讶,心中却是一凛。
“怎么说的?”陈易冷笑一声,声音不大,却带著刺骨的寒意,“你让我去送死,还问我怎么说的?若非我及时跑了,早就交代在那,岩坎老板,我替你跑腿,差点把命丟在蛮子手里,这笔帐,怎么算?”
岩坎脸上的笑容有些掛不住。
他飞快地权衡了一番,此人能活著回来,倒也有几分眼力和警惕,命也够硬,如今还大摇大摆地上门算帐,看来那些人並没有执意追杀,其中发生什么,
叫人不得而知—
他一时未往陈易將四人全杀了去想,能做到以一敌四並且全身而退,早就是王府止戈司的王牌,名扬南巍,岂会来他这赌得倾家荡產?
如此一来,最大的可能是,那边把他当作一个可用之才,刻意放回·
“哎哟,误会!天大的误会!”岩坎一拍大腿,站起身,显得无比愧疚,“陈兄弟,那帮蛮子不开化,谁知道他们发什么疯!老哥我对天发誓,只是想让你去熟悉熟悉路,顺便嘿嘿,看看有没有別的財路。哪成想他们敢动止戈司的人?真是反了天了!”
他一边说,一边观察著陈易的表情,见他眼神依旧冰冷,心中念头急转。
“这样!”岩坎一咬牙,一旁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又拉开抽屉取出一叠银票,推到陈易面前,“兄弟你受惊了。这两百两银子,外加一千两的银票,算是老哥给你压惊,赔个不是!往后,咱们合作的机会还多著呢。”
陈易的目光在那堆钱財上停留片刻,脸色似乎化开了一丝,他掂量了一下,
揣入怀中,淡淡道:“岩坎老板倒是爽快。”
见陈易收了钱,岩坎心中大石落地,笑容重新变得热络道:“应该的应该的!陈兄弟是干大事的人,往后老哥还得仰仗你。来来来,今天手气肯定旺,玩几把?”
能用钱安抚住的人都不难对付,岩坎最不缺的便是钱,这买卖不亏,甚至陈易能全身而退,更证明了其人的价值,值得拉近器重。
“好说、好说。”
陈易揣著钱袋,拋了又拋。
一连几日,这止戈司新人似乎完全沉溺在了赌坊的纸醉金迷之中,他出手阔绰,身边环绕著赌坊里最妖嬈的女子,贏多输少,春风得意。
岩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甚至暗中吩附手下荷官,让陈易“多贏点”,越赌越上头,越上头越赌,这种人他见太多,陈易正是其中一个。
赌坊暂时收市,陈易大手回笼著桌上筹码。
“陈兄弟手气旺啊!”
岩坎端著酒杯凑过来,笑容满面,
“有件小事,还得再麻烦兄弟你跑一趟。”
陈易推开身边的美女,斜睨著他:“哦?又是送人?”
“对对对!”岩坎压低声音,“还是上次那帮朋友,又有两位长老要去一个地方,这次路线更熟,也更安全!兄弟你只需护送他们到指定地点,跟上次一样,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顺利过去就行。事成之后,这个数!”他比划了一个手势,比上次更加诱人。
陈易沉默了几息,道:“行。”
依旧是风雪交加的荒山路。
两名裹在厚重黑袍中的异端长老,在陈易的“护送”下沉默前行,气氛压抑得如同冻结的空气。
走到一处陡峭的隘口,风声鸣咽。
陈易忽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其中一位长老警惕地问,声音嘶哑。
陈易缓缓转过身,没有回答,只是抬起了手。
剑气无声。
寒光乍现即隱。
两颗包裹在黑袍中的头颅,带著凝固的惊,滚落在冰冷的雪地上,鲜血迅速在白雪上晕开两朵刺目的红。
陈易看也没看尸体,转身消失在风雪中,只留下一地狼藉,血腥迅速被风雪掩盖。
“陈兄弟,人送到了吗?”
“送到了,这一回简单多了。”
“老哥没坑你吧?”
“老哥义气!”
“嘿,你跟我义气不义气,老哥在这赚这么久的钱,义气是本份,整体想的就是带兄弟赚钱,来,拿著!”
“这,太多了———”
“拿著!”
“以后,哪怕货被逮了,人被捉了,我陈明也绝不拖你下水,走江湖,讲的就是一个道义!”
“你这话就见外了,真拖了老哥下水,老哥我也绝不会说你一句不是。”
“老哥!”
“老弟!”
某一日。
赌坊的喧囂被一阵沉重而压抑的脚步声打断。
三个身著奇异黑色劲装,脸上带著挣狞金属面具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
他们身上散发著冰冷、血腥的气息,与赌坊的乌烟瘴气格格不入。
管事一惊,忙不迭地点头哈腰,將这几人迎去静室雅间去见岩坎。
为首的面具人,声音如同金属摩擦,冰冷刺骨:“岩坎头人。”
岩坎心头一跳,连忙起身,脸上堆满討好的笑容:“使者大人!什么风把您几位吹来了?快请坐!”
面具人旋即就坐,岩坎双手给几人奉茶,隨后在对面坐下。
“好茶,岩坎头人好品味。”
“哎呀,多亏你们关照,否则我也喝不了这么好的茶。”岩坎殷勤回应道:“都是沾光、都是沾光,待会要不玩一两把?”
“玩就不必了,这一回顺路过来,只是问两句。”
“什么事值得顺路问?是今岁上贡的钱两要再加?”岩坎面仍掛笑,心却有点滴血。
面具人摇摇头,岩坎鬆了口气,又疑问道:
“那么是?”
“你向来得力,办事也少有差池,只是这段时间”面具人顿了顿道:“几次护送的长老都迟迟未归,你有什么头绪吗?”
岩坎先是皱起眉头反问道:“那使者你又有什么头绪吗?”
问完之后,他才后知后觉地愣了一愣。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化,冷汗刷地一下就冒了出来,道:“七七位?都都迟迟没到?不可能啊!过关的人不能多,我都是派最靠谱的人办的,这、
这—”
“靠谱?”另一个面具人发出夜梟般的冷笑,从岩坎的神色里捕捉到什么,
声音显出一丝杀意,“我们这七个人里,可没一个回来。”
“但確实每次都把人送过关了!我那边有插人去看,”岩坎回应道,“这里面怕不是有误会!说不定是路上出了別的岔子..”
“不要惊慌,你忠心耿耿,我们不是来为难你。
岩坎意识方才失態,端回镇静,笑了几声,旋即道:“那几位放心,这事我必定查明,等会就给几位一个初步交代。”
说罢,他起身道:“我这就叫人进来问,跟他说进来拿钱,我当面问个明白。”
咚、咚、咚!
兀然的敲门声响起,岩坎赔笑了一句,“哎哟不用叫了,一看就是赌输了。
说罢,便拉开了门。
那道身影一跨入门內,岩坎就喝声发难:“谁让你拍门,还有没有规矩?!”
“啪!!”
他话刚说完,迎面就给甩了个大耳光,愣了下后怒从心起,正要喝骂,又给甩了个大耳光。
岩坎退了两步,人被打懵了,一屁股跌坐在地。
“止戈司办案,”陈易举起手中腰牌,“还请岩老弟不要不识时务。”
岩坎瞪圆了眼睛,僵在原地,气血上涌,顷刻昏死了过去。
陈易反手砰地一声关上雅间的门,隔绝了外面赌坊的喧囂,昏黄的灯光下,
他隨手將岩坎昏的身体踢到角落。
他的闯入,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那三名原本端坐的面具人,剎那已然弹身而起,
冰冷的金属面具下,目光如同实质死死钉在陈易身上。
雅间內的空气骤然凝固。
为首的面具人最为高大魁梧,他反手从背后抽出一柄造型奇特的武器,那並非寻常刀剑,而是一根近五尺长的黑金属骨笛,左边身形瘦削者则往腰间一抹,指间已多了十枚闪烁著暗绿幽光的飞鏢铁梭,右边的面具人则从腰间拔出一对沉重的后背弯刀。
三股截然不同却同样致命的杀气,如同三张无形的大网,瞬间將陈易笼罩其中。
陈易周身衣衫无风自动,无形的剑意如同水银泻地,精准而霸道地切入那三股合围的杀气之中,竟硬生生在密不透风的杀局中撑开一片属於自己的天地。
他脸上的表情却依旧淡漠,他看都没看那三个如临大敌的面具人。
陈易隨手拿起一个乾净的茶碗,拎起茶壶,滚烫的茶水注入碗中,发出轻微的声响,格外刺耳。
他端起茶碗,凑到嘴边,轻轻吹了吹热气,然后不紧不慢地啜饮了一口。
陈易放下茶碗,眼皮都没抬一下,淡淡地吐出一个字,“坐。”
仿佛他在请三人做客。
三名面具人一时惊疑,杀意虽未减,动作却不由自主地顿住了,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此人面对他们三人合围,竟如此托大?
“阁下何人?意欲何为?”为首持骨笛的面具人声音冰冷,带著金属摩擦的质感,打破了僵持。他没有坐,骨笛尖端依旧遥遥指向陈易要害。
“听到里面吵架,”陈易语气平淡,“就进来看看。”
“哼,装神弄鬼!”手持双刀的暴躁面具人忍不住怒喝,“说!我们的人呢?都被你弄到哪里去了?”
“人?”陈易目光扫过三人,“死了。”
“什么?”三个面具人同时失声,即便隔著面具,也能感受到那股惊怒,愈发杀意横生。
“都死了。”陈易的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雪山上,隘口边,林子里——.你们的人头,滚得满地都是。”
“你找死!”双刀面具人再也按捺不住,狂吼一声就要扑上,却被持骨笛的首领用笛身一横,强行拦住。
“慢著。”首领面具人死死盯著陈易,“你————为何要与我等为敌?”
“为敌?”陈易轻轻笑了一声,“你们也配?”
“你到底是谁?!”
片刻,那人一字一句,清晰地吐出几个字:
“前西厂千户,陈易。”
话音落耳,三人皆是身体剧震,瞳孔在面具下骤然收缩到极致。
一瞬间,之前所有的疑惑都有了答案,为何那七人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对上此人,別说那七人,就算他们三个此刻都不一定是其敌手..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瞬间从尾椎骨直衝头顶。
雅间內,顷刻死一般的寂静。
许久,为首的面具人微不可查地晃了晃,似乎找回一丝镇静,他注意到陈易虽然剑意沛然,却也·並未表露下一步的杀意·
“陈—-陈千户。”他换上了敬称,骨笛尖端不自觉地垂低了几分,“敢问为何?为何要杀我神教长老?”
陈易放下茶碗,指尖在粗糙的碗沿上轻轻划过,平淡道:
“杀几个嘍囉,自然是为了引起你们这些管事的注意。”
“引起注意?”用七条人命来做敲门砖,持双刀的面具人不住悚然。
为首的面具人抬手制止了同伴的躁动,死死盯著陈易的眼睛,试图从中分辨真偽:“陈千户此言何意?我等不明白。”
“你们,”陈易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扫过三人,“是那所谓神教的『异端”,是么?”
“异端?”为首的面具人愣了一下,隨即发出一声低沉嘶哑的自嘲,“呵在那些偽信者的眼中,我们的確——-是异端!”
他的声音里透著一股被压抑的愤薄以及某种扭曲的骄傲。
“那就对了。”陈易的声音没有任何波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哪怕不是,也至少可以谈谈。”
“敌人的敌人?”面具人首领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陈千户的敌人是?”
“安南王。”陈易吐出这三个字时,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名字,但雅间內的温度仿佛骤然又降了几分。
“安南王?”为首的面具人一时失声。
这个答案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安南王府掌控整座南巍三百余年,连诸土司也摄於其淫威苦不堪言,以眼前这位前西厂千户的凶名,与权倾一方的藩王结下死仇,倒也並非不可能。
“陈千户此言当真?”首领面具人声音凝重陈易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拋出了另一个名字,一个带著血腥味的名字:“秦威年,你们知道么?”
“.—秦威年?”面具人首领显然知道此人,“那位·以宽厚博闻、礼贤下土著称的秦氏族老?前些日子—·因捲入宗庙行刺案,已被王府著令梟首示眾——“
他的语气带著一丝惋惜,也有一丝疑惑,不明白陈易为何突然提起这个已死的王府中人。
“是他。”
陈易的声音依旧平淡,端起茶碗,却没有喝,只是看著碗中微微晃动的茶汤,仿佛陷入了回忆“他对我,有知遇之恩。”
话音虽然平淡,却沉而有力。
“敢问千户——.其中缘由。”“
“他慧眼识珠,不拘一格,自龙虎山暴露行踪,我又被朝廷追杀,一路入南疆,举目无亲之际他仍然险胆起用如我这般来歷不明之人。
我与安南王,新仇日恨,”
他一字一句,双目如火,
“所以—不刃不休。”
为首的面具人急速消化这惊人的信息,末了,他权衡利弊一番,对著陈易微微頜首,比之刘恭敬了不止一分。
“陈千户所言,事关重险。此事非我等三人可决断。”他措辞谨慎,“我等需即刻返回总坛,將千户之意,稟明上圣。亥上圣有意,自会有人在此与千户联π,不知千户意下如何?”
“可。”那人只回了一个字。
三名面具人不再多言,对著陈易略一抱拳,悄无声息地拉开雅间的门,犹如融入阴影的亜魅,迅速消失在赌坊外嘈杂的夜色中。
陈易端起茶碗,將碗中早已冰凉的茶水一饮而尽,眶当一声,他隨手將茶碗丟在桌上“你跟我,不双不休?”
秦青洛端起茶水,侧眸问道。
“当真如此?”
“下官的確是这般说的。”
“应变得不错。”
陈易闻言抬起眸,不知为何,女王爷嘴角似有一丝微不可的笑意。
撩到了。
確实不错。
陈易深吸一气,遂有些侷促地辩驳道:“下官只是-依计行事,並非有意討好王爷。”
都怪小狐狸的错,有时他不得不很不得不地承认,自己秉性里的確有那么一丝丝微不可察的傲娇。
既然如此,顺势而为才显得真诚。
高险女子呵了一声,仍旧斜他,於是陈易愈发显得窘迫。
这是从未见过的秦青洛眸光微敛,如他这般的人,竟也会窘迫?
她常年来摸不透陈易,世上如他般执迷色相却心念旧情的人何乏之少,叫人难以把握,只能说是奇男子,眼下比之刘相近了些,忽觉他乏实很好摸透。
那不妨,再摸透一些。
秦青洛深深看了陈易一眼,隨后托起烛台出门,陈易紧紧跟上。
她出了书房,往书么直去,二人再度见到顶处么台的宽阔风景,烛光之下,
夜空星罗棋布,萤光炼烁,四面八方的山峦如起携的海洋,王府如险舟半边没水,这是一幅美得惊人的景色。
秦青洛吩咐婢女送酒来,隨后问道:“你酒量如何?”
“不太喜欢喝酒,但提碎玉龙为君尚且容易,何况喝酒?”
“殷勤。”秦青洛笑一声,特意命人开封窖中佳酿。
陈易没仔细去听是哪种酒,对他来说都一样,他確实不喜欢喝酒,一直以来喝酒都是陪別人喝,陪得最多的就是閔寧,乏次就是...秦青洛?念及此处,陈易不免有点惊奇。
不一会,酒便送上么台,婢女为二人斟上了首轮酒水后,便被秦青洛隨手屏退下么。
陈易起身与硕人碰杯,问道:“王爷眼下是想对酒谈武意?”
“不急。”秦青洛道。
二人便將酒水一饮而尽,隨后眺望远方风景。
“寡人初明本心时,你我便在云上活酒。”她忽然道。
陈易微微一愣,这还是她头一回与他谈起往事。
那时近乎身陷绝境,他与这女王爷不不休,怨仇介天之下,他如何记不得活酒之后王爷王妃先后起的事?
送命题啊,
这该如何是好?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