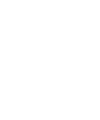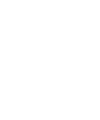归义非唐 - 第544章 革故鼎新
第544章 革故鼎新
“混账!混账!混账……”
洪武十一年九月末梢,在刘烈返回洛阳的同时,南诏也在高骈的手段下,境况渐窘起来。
群蛮在汉军的“厚赏”下,从入夏开始就不断袭击南诏的移民队伍,致使南诏军队疲于奔命。
对于群蛮从南诏手中掳掠的汉人,高骈则是开出每人两口铁锅,亦或者两石粮食的高价。
在厚赏和过往的仇怨下,群蛮对南诏的袭击层出不穷。
对于移民中的汉人,群蛮则是宝贝似的留下来,但对于南诏治下的乌蛮和白蛮百姓,他们就不是那么友善了。
从阳苴咩城到丽水城足有九百多里路程,沿途都是横断山脉和原始密林,以丽水节度使手中的兵马,着实难以护住沿途所有百姓。
更何况此时瘴气频发,哪怕是早已习惯永昌、阳苴咩城气候的百姓在穿越哀牢山和高黎贡山时,也不免会染病身亡。
正因如此,祐世隆想要转移实力的计划,不可避免的遭到了破坏。
阳苴咩城的五华楼内,董成看着气愤的祐世隆,心中也不免叹了口气。
“过去数月中,永昌十余万百姓迁往押西城路上因为疫病和群蛮袭击而死伤两万余人,阳苴咩城所迁往押西城而存活者不足九万……”
“六诏故地,尚有二十余万百姓未曾迁徙,若是群蛮继续袭击我军,恐怕能迁往永昌、丽水的百姓不足十五万。”
南诏已经丢失了不少地方,加上南边的黑齿、棠摩、獠子、和蛮、金齿等部落相继投降高骈,南诏所辖疆域只剩下战前的三分之一了。
祐世隆心生绝望,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真的倒下,因此他看向董成,踌躇道:
“朕欲让隆舜前往押西城,汝以为如何?”
“甚好。”董成不假思索的点头,但又担心道;“只是王少年心性,恐怕……”
隆舜是祐世隆的儿子,但由于祐世隆常年在外征战,因此对隆舜的教导不足,导致隆舜性格十分贪玩。
这种性格如果没有贤臣辅佐,很有可能给未来的南诏带来灭顶之灾。
只是除了隆舜外,祐世隆剩下的几个孩子都只有十几岁,显然不能担负重任。
想到这里,祐世隆心生颓靡,而董成也开口道:“陛下可前往永昌坐镇。”
见董成这么说,祐世隆便知道,董成是担心自己与阳苴咩城共存亡。
祐世隆确实有这种想法,但面对不成器的儿子们,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马上就要入冬了,若是不出预料,高骈兴许就要出兵攻打龙和城了。”
“如果龙和城、石桑城都被攻破,那朕便前往永昌。”
石桑城距离阳苴咩城三百余里,祐世隆有足够的时间撤往永昌。
从拓东到永昌足足八百余里,而这恰巧就是汉军在粮草、民夫充足下,能远征的最远距离。
在祐世隆看来,届时高骈顶多就是打到阳苴咩城,然后继续在阳苴咩城,开垦旧六诏的山间平原。
这些山间平原大大小小十几个,林林总总加起来,已经有了四百余万亩耕地,能开发的都被开发差不多了。
若非如此,南诏也不会向东、西两个方向开拓。
哪怕如今永昌、丽水等处有数十万百姓,上百万亩耕地,但终究不如已经被开发彻底的六诏精华。
更何况随着祐世隆带人西迁,届时南诏必然耕地、粮食不足,只有向西发动战争,将西南刚刚恢复些许元气的骠国诸多城邦作为养料了。
“唉……”
祐世隆长叹口气,心气似乎被这些消息打散。
几日后,六诏最后的百姓也被强行迁徙永昌而去,不过其中也有相当多的百姓选择留下来。
为了躲避搜捕,他们躲入山中,使得本就兵力不足的南诏只能放弃他们。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而随着冬季降温愈发明显,蛇虫鼠蚁身影渐渐变少后,战事自然而然的在十月初爆发了。
“轰隆隆!!”
十月初二,随着汉军休整差不多后,高骈联合李阳春所部的兵马,留驻万余兵马后,以五万兵马、十万民夫继续发起了对南诏的作战。
二百门火炮在龙和城以东作响,沉重的铁炮弹将这座山城打得碎石飞溅。
城内的近万南诏兵马只能龟缩不出,而高骈与李阳春也选择啃下这个硬骨头。
“朝廷从后方起运三百万石粮食,起码能运抵三十万石到昆明。”
“我军在云南等处军垦,如今积存二十余万石粮食,起码能支撑我军收复故六诏之地,届时祐世隆必然会逃亡永昌。”
“因此我军需要再阳苴咩城军垦,待到来年入冬再发兵收复高黎贡山以东的诸多汉地。”
龙和城东的汉军营帐内,听着帐外的炮声,高骈与李阳春、王建、葛从周、张归霸等人述说着自己的见解。
李阳春兴致不高,其余人也脸色凝重。
他们之所以如此,全因身为阆中郡公的邓俨在半个月前因瘴病而薨于卧榻,享年三十八。
这个年纪放在将领中应该正直壮年,但由于邓俨从安南攻入通海染上瘴气,他只能长眠于此。
两路攻打通海的计划是李阳春制定的,他眼下自然兴致不高,满脑子想的都是应该如何对邓俨父母及妻儿解释。
汉军痛失大将,李阳春只能让刘松与张归厚驻守通海,他自己率葛从周、张归霸、庞师古等人北上与高骈汇合。
“此事全听高王做主……”
李阳春对高骈的计划没有什么格外的见解,此刻他只想着如何回到牙帐,写信向邓俨妻儿老小解释。
“既是如此,那便以此计对付南蛮。”
高骈也知道痛失挚友与大将的心情,他没有久留众人,只是颔首后遣散众人。
随着众将离去,高骈也开始继续指挥起了汉军,而汉军西进的速度也绝对不慢。
十月二十二日收复龙和城,二十五日攻打石桑城,冬月十二日收复石桑城,祐世隆率军队西逃永昌,火烧阳苴咩城。
腊月初三,高骈领军与张武会师阳苴咩城,兵分收复剑川、银生等处,杀蛮兵二万众,群蛮皆降。
“好,阳苴咩城收复,明年入冬差不多就能收复高黎贡山以东的永昌等处了,两年时间将高黎贡山以东尽数收复,时间尚可。”
腊月末梢,随着西南捷报不断送入洛阳,贞观殿内的刘继隆则是心情七上八下,最后看懂汉军收复永昌以东的疆域后,这才松了口气。
“敕令,追封益昌郡公、岭南都督都司同知邓俨为南海郡王,以其子邓隆袭定国公,世袭降等。”
邓俨是刘继隆在临州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学校时平平无奇,但后来在收复齐鲁、江淮、岭南时出力甚多,获封益昌郡公。
刘继隆原本想过,此役结束后便将他拔擢为国公,不曾想他染上瘴气,英年早逝,只留下了邓隆、邓愈、邓越三个儿子。
眼下将他追封为郡王,让他长子邓隆袭定国公爵,也算是弥补了。
想到此处,刘继隆长叹口气,接着又继续敕封道:
“以渤海郡王高骈为太尉,加授三千户食邑,越国公李阳春拔擢为临洮郡王,加授巴川郡王张武为太保,食邑增千户。”
“诸如郡公刘松、王建及诸多有功之臣,有爵加爵,无爵授爵,令太子拟个章程出来。”
刘继隆交代过后,西门君遂连忙应下,而刘继隆也起身在殿内走动起来,活动身体。
他在活动身体的时候思考接下来的大汉应该如何走下去,直到一刻钟后有脚步声从殿外传来,他才缓缓抬头看去。
“千岁……”
“陛下千万岁寿!”
只见刘烈带着郭崇韬、严可求二人和几名抬着木盘文册的内侍走入殿内。
几人见到刘继隆后,纷纷朝他行礼作揖,而刘继隆则是颔首道:“京畿道的事情,处置好了?”
“回阿耶,已经处置好了,这些便是处置的结果。”
刘烈侧过身子,将那数十本文册显露出来,同时踌躇道:“只是京畿道那十五家勋臣,儿臣……”
显然,对于西国公厝本等人的处置,他还是十分小心的,毕竟这群人都和刘继隆打过天下。
对此,刘继隆则是看向他:“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依照《大汉律》处置便是。”
“是……”刘烈闻言颔首,随后从内侍端着的木盘中取出文册,双手呈给刘继隆。
他已经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自家阿耶要自己处理,他便把这本文册带走。
如果自家阿耶让自己处理,那则是将这本文册呈出去。
刘继隆并未有什么表态,只是从他手中接过了文册,随即当着他的面翻阅起来。
文册中,十五家勋贵依罪分为三等。
十五家勋贵,无一例外都做了隐匿田亩、偷漏赋税的事情,而将他们分为三等的凭据则是在这些事情基础上,有没有出现命案、欺压这种事情。
英国公王思奉,其子王怀恩纵容家仆害命三条,淇国公刘英谚之子刘蒯害命一条,西国公厝本之子钦德纵容家仆强掠民田七百余亩……
按照《大汉律》,英国公王思奉降爵县伯,其子王怀恩及害命家仆处斩。
淇国公刘英谚降爵为县公,其子刘蒯处斩,而西国公厝本降爵位郡公,其子钦德流配……
除了这些,其余十二家勋贵,对于直接犯事的勋贵本人则是去爵,若是子嗣犯事则勋贵降爵,子嗣依照《大汉律》处斩或流配。
面对文册上的内容,刘继隆沉默不语,他并不觉得这些刑罚判得重,甚至觉得有些轻了。
《大汉律》自洪武元年编修,废除了许多肉刑和奴仆的刑罚,加强了贪腐和官员犯事的惩处。
由于数量较多,刘继隆并未亲自翻阅,直到今日他才知道,勋贵犯法是可以用爵位来抵罪的。
“阿耶?”
刘烈小心翼翼的开口询问,显然是担心自己处罚的过重了。
刘继隆抬头看向他,张了张嘴,本来想要让他从重处罚,可回想起厝本、刘英谚、王思奉等人跟随自己征战的场景,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原来处理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刘继隆在心中苦涩感叹,末了才叹气将文册递回给了刘烈:“便按照如此操办吧。”
其实按照《唐律》的“八议”与“请减赎”来说,《大汉律》已经算得上进步了,至少在《唐律》中,犯事的勋贵子弟是可以用官当和减赎来将死刑减轻为流配或削官的。
但是在《大汉律》里,除了勋贵本人可以用爵位来抵除本人罪刑外,其它官员和勋贵子弟只有按律论罪。
正因如此,《大汉律》下的刘蒯等人必须死,所以刘烈才会如此小心翼翼。
毕竟按照《唐律》,刘蒯等人完全可以出钱来减罪,其父也不用降爵。
如今有了刘继隆点头,刘烈便将心放了下来,但很快刘继隆的话又让他提起了心。
“云南最迟两年后便会彻底平定,京察的事情不能再继续耽误下去了。”
“今岁学子即将毕业,临州大学的学子也有两千余人返回洛阳。”
“汝好好调派这些人,朕等汝的消息……”
刘继隆的话令刘烈及他身后的众人感到头皮发麻,毕竟刚刚收拾了十五名勋贵和数百名有品秩的官员,他们甚至还在头痛应该如何收尾,结果皇帝又要派给他们更为得罪人的差事。
这次可不是局限于地方一道了,而是要面对整个天下诸道,面对所有勋臣官吏……
想到这里,刘烈只能硬着头皮:“儿臣定不会让阿耶久等。”
“下去吧。”
刘继隆吩咐过后,转身便往金台继续走去,而刘烈则是让内侍将所有文册放下,随后才带着郭崇韬与严可求离开了贞观殿。
返回东宫的路上,刘烈与郭崇韬、严可求三人尽皆面色凝重。
方才在宫中所受的旨意,此刻如同一块千斤巨石,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连沿途官吏对他们躬身行礼都被他们三人无视。
两刻钟后,随着他们回到东宫,早已在殿前迎候的赵光逢立刻察觉到了异样。
他见三人神色凝重,心中便是一沉,连忙上前对刘烈恭敬作揖,语气温和的同时却带着不易察觉的担忧:
“殿下,可是陛下对京畿道的处置……有所不满?”
“阿耶并非不满,只是……”刘烈摇头回应,脚步未停的走向东宫正殿,示意赵光逢进入殿详谈。
在他的示意下,三人跟着他走入殿内,而张承业眼见情况不对,当即便屏退了左右。
随着张承业亲自动手将殿门合上,四人此刻才感受到了安全,但刘烈却并未立刻坐上主位,而是负手来回渡步,似乎在思虑什么。
片刻后,刘烈这才停下脚步,语气带着难以言喻的疲惫与沉重:“阿耶……要某等如京察京畿那般,京察天下诸道。”
“亦或者,比要在京畿那时还要严苛……”
一句话,如同冰水泼入滚油,瞬间在殿内炸开。
赵光逢一向沉静的脸上也骤然变色,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瞬间感受到了这件事的棘手。
京畿道这一趟,他们已是将关中的勋贵得罪了个死尽,如今陛下非但没有叫停,反而要将这燎原之火燃遍天下。
这已不是刮骨疗毒,简直是欲将天下官场推倒重来!
这其中牵扯的利益网、关系网,盘根错节,深不见底。
这差事,已不是得罪人,而是要与天下大部分的既得利益者为敌。
若是可以,赵光逢真想劝刘烈不要接下这件差事,但这是皇帝的旨意,无从抗拒。
更何况,此事对于刘烈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危局,亦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唯有将这事办得铁板钉钉、漂漂亮亮,太子的地位才能真正稳固,他们这些东宫旧臣,也才有拨云见日,执掌中枢的那一天。
想到这里,赵光逢将那份惊悸强压下去,神色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只是眉头依旧微蹙。
“殿下。”郭崇韬在路上已经想了许多事情,加上他性子较急,因此他率先开口:
“此事虽难,却不得不为,更是大利于我大汉之举!”
“如今开国虽不过十一载,然前唐以来,庙堂早已适应吏治腐败,地方更不重视勋贵豪强兼并土地。”
“此次京畿道之行,殿下也看到了,那些昔年陛下所安排的平民官员在贪腐受贿这块,比前唐旧官也不遑多让。”
“仅仅处置京畿,固然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然地方诸道有司终究有藏污纳垢之处。”
“如今若是能京察解决这些贪官污吏,对于殿下日后治国亦有好处。”
“此外,若是能京察天下,朝廷可获巨量田亩钱粮,以此充实国库。”
“亦可将那些罪囚冗吏,尽数发往辽东、大宁、云南等处实边,助陛下开拓边疆之国策成功。”
“再者,若是此事能成,殿下之威望将如日中天,储位坚若磐石!”
面对郭崇韬的这番话,刘烈等人尽皆颔首,严可求更是接话道:
“郭公所言,乃阳谋大势,诚然不错,但其弊亦显而易见。”
“我等此番若是京察天下,那便是要将天下勋贵豪强得罪至死。”
“即便我等是奉旨行事,秉公执法,这些勋贵豪强亦会将这断财之路、破家之恨,记在我等头上。”
殿内一时沉寂,唯有炭火在兽耳铜炉中噼啪作响。
对于豪强勋贵来说,他们自然不敢对刘烈动手,但帮助刘烈的这群人就不好说了……
面对严可求的这番话,赵光逢则是结合二人所说,稍微思考过后便温言打破了沉默:“利弊皆已分明。”
“只是在某看来,这弊端并非无解。”
他目光看向刘烈,对其作揖道:“只要殿下能顺利克承大统,今日一切仇怨,届时皆可化为乌有。”
“勋贵豪强再能,也不敢与继承大统的殿下算账,而殿下则可庇护某等。”
“只要殿下牢牢掌握着张氏和曹氏等少数几位郡王的支持,便是将领浮躁,亦不敢起兵作乱。”
“故此,眼下重中之重,非是忧惧日后,而是如何将这件‘得罪人’的差事,办得无人能指责,办得让陛下彻底满意。”
他的话,如同拨云见日,将问题的核心赤裸裸地摊开在了众人面前。
只要皇帝满意这件差事,刘烈日后必然继承大统,那些勋臣官员便只是跳梁小丑。
想到此处,刘烈的目光扫过三位心腹谋臣,最终重重一点头:“赵先生所言,深得吾心。”
“阿耶要的是结果,是一个清明的天下,更是实边所需的那数十万罪民。”
“诸位先生且说说,这京察天下之事,又该如何着手?”
对于刘烈这番话,郭崇韬立刻表态道:“眼下已是腊月,再过半月,国子监及各地官学便有数万学子完成学业,候官候选。”
“这些人年轻气盛,尚未被官场染黑,正是一把快刀。”
“依臣所见,殿下可按照先前陛下所言,从中遴选锐意进取、家境清寒者,充入京察队伍。”
“此外,临州毕业即将归来的那两千余学子更精通刑名钱谷,用起来比新人更为老辣!”
“是极。”严可求点点头,附和着郭崇韬的话,同时补充道:“人手可解,方略却需调整。”
“京畿道之标准过于宽松,若欲达成陛下所需之规模,牵连标准必须放宽,如此才能牵连更多的罪民。”
他声音平静却说着最酷烈的话,但众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赵光逢更是补充道:
“话虽如此,律法尺度,必须明发天下,让所有人知道因何而罪,而非暗箱操作,此谓阳谋杀人,使得他们心服口服。”
“此外京畿道判决既然已经下来,那便先开始造势,让各地报社将此次殿下所查案例、判决,择其典型,刊印成册,发于报纸之上,以示朝廷绝非滥施刑罚,而是有法可依,有罪必惩。”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一条清晰而冷酷的战略逐渐成型。
以放宽标准扩大打击面,以新生与沉沦之吏为爪牙,以明发律令为旗帜,最终达成皇帝所需的“人口”与“田地”两大目标。
刘烈听着三位属官将一项项细则完善,原本凝重的脸色也渐渐舒展,最后笑着点头道:“如此便依诸位先生之策,只是还需要劳烦诸位先生奔波。”
“郭先生,劳你即刻草拟征调学子与临州旧吏的章程。”
“严先生,由汝主持官吏从《大汉律》中挑选条例,拟定《京察天下诸道量刑则例》,将标准明晰。”
“赵先生,以报社报纸引导舆情,行刊发之事,便交由汝统筹,此外再请卢先生将京畿之事妥善解决后,立即带领京畿道诸多京察队伍听令,等待入剑南道京察。”
对于刘烈的安排,三人齐齐躬身:“臣等领命!”
刘烈看着他们,郑重拱手:“孤之前程,大汉之社稷,尽托付于三位先生了。”
郭崇韬、严可求、赵光逢三人连忙作揖回礼,接着便在刘烈注视下离开了东宫。
“噼里啪啦……”
腊月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新年的喜庆气氛却被另一种更加炽烈的情绪所取代。
洪武十二年的开端,神都洛阳的街巷里弥漫着的,不再是年节的欢腾,而是一种压抑的嗡嗡低语。
自洪武三年刘继隆力排众议,在天下各州县广设官学以来,如今已是第九个寒暑。
寻常百姓家的孩子,纵使无法如富家子弟般十年寒窗求取功名,但也能送进去读上两三年书,识得几百常用字,会写自己姓名,看懂官府告示。
这点滴的教化,于国而言是开启了民智,于民而言则是多了一扇窥见世道的窗。
正是因为天下官学推广,因此朝廷开办的报纸才能被平民所读懂,为平民添了处看不到的风景。
这报纸在此前并未展露什么威力,可随着洪武十二年到来,正月新年这期报纸却登载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内容。
《国报》与《京报》的头版,赫然便是《京畿道京察结果昭示天下》,其下罗列着密密麻麻的案例,判决……
这在报纸上,所有官吏贪腐和勋臣害命的案件时间、地点、人物、赃款数目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除此之外,此事末尾还有个的惊人数字,那就是此次京察共抄得钱粮五百余万贯,粮秣七十余万石,田产一百七十余万亩,其余古玩珍宝逾千箱……
识字的人在拿到报纸后,立马便说给四周不识字的人听。
他们每读出一条,四周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呼和咒骂。
议论声、咒骂声、诉苦声,在洛阳城的每一个茶肆、酒馆、街头巷尾中汇聚、发酵。
平日里逆来顺受的沉默,在这一刻被报纸上的白纸黑字点燃了。
他们骂那些蛀虫般的贪官,恨那些趴在他们身上吸血的勋贵,更抱怨着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公。
宰相崔恕的马车,就在这片压抑的鼎沸人声中,缓缓行驶在回府的路上。
尽管车窗紧闭,但车窗却隔不断窗外那一声声清晰的、咬牙切齿的议论。
崔恕靠在粗布制成的软垫上,尽管闭着眼,可外面的声音毫无阻碍地钻进他的耳朵。
“直娘贼,某便是卖一辈子茶都卖不出这贪官污吏的碎末。”
“还是太子殿下厉害!查得好!就该把这些祸害全抓起来!”
“不知道啥时候能查到洛阳来……”
窗外的声音不断传来,使得崔恕指尖微微颤抖。
东宫那边的事情,他也曾听说过,近来许多临州毕业的学子都被召到了洛阳,并授予了都察院、六科、大理寺和刑部等处的官职。
这些种种行为似乎都在告诉崔恕,所谓京察并未结束,自家陛下的野心也并没有那么小。
到了今日,听着窗外的那些声音,崔恕总算是明白了。
陛下确实不准备就这样停下京察,而太子也即将把京畿道的这把火扩散到其他地方。
想到这里,崔恕渐渐有些不安,所以在回到府邸后,他第一时间便召来了家丞,对他吩咐起来:
“告诉族中的那些子弟,多看看报纸,近来小心行事。”
“若是出了事情,便是老夫也护不住他们。”
交代清楚后,崔恕接下来的日子便开始小心谨慎的正常上下朝,而类似他这样的人也并不在少数。
厝本、刘英谚、王思奉等人的下场还历历在目,他们都不想成为下一个被当做典型的勋臣。
只是有些事情,并非他们想不想那么容易,树大根深的家族只要烂了一处树根,整棵树就会都跟着倾覆。
没有人可以完完全全的掌控另一个人,更别提一整个家族了。
正因如此,随着大半个月的造势结束,刘烈也趁热打铁的找到了刘继隆。
“此便是儿臣与几位先生所拟定的《京察天下诸道量刑则例》,请阿耶过目。”
贞观殿内,刘烈递出自己的奏表,由西门君遂转递给了刘继隆。
刘继隆看了看其中内容,发现这次的量刑显然比上次要高后,不由得点了点头:“人挑选的如何了?”
“已安排了一千四百五十二名官员,四千七百五十二名吏员,随时可以派出京察天下,只是……”
刘烈顿了顿,目光看向刘继隆后才小心开口道:“还请阿耶发下北衙六军的鱼符与旗牌,儿臣准备以郭崇韬、卢质、严可求、赵光逢等人巡查诸道。”
“此次巡查,从河西、关内、河东、东畿、河北等五道开始,诸部向南而去。”
刘烈说罢,刘继隆便不假思索的点头,目光看向西门君遂:“将北衙六军的旗牌和鱼符交给太子。”
“奴婢领命……”西门君遂应下,随后派人将鱼符和旗牌送往了东宫。
见到北衙六军的兵权到了自己手里,刘烈不由得松了口气,毕竟北衙六军三万人,足够保护六千多官吏京察了。
“听闻太子妃有了身孕?”
刘继隆看着刘烈紧绷的样子,试图与他说些家常,但刘烈却依旧紧绷。
“已有两个月身孕,等儿臣凯旋而归时,大概便临盆了。”
刘烈公事公办的说着,让刘继隆渐渐有了种疏离感。
兴许是接触刘继隆太近,亦或者是年纪稍长,懂得了君臣有别,总之刘烈此时对刘继隆有了种畏惧感。
这种畏惧感不是子对父的畏惧,而是臣对君的畏惧。
刘继隆心里猜到了这种疏离感的原因,心里有些失落,却也有些欣慰。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是沉默着,直到刘烈请辞,他才微微颔首应了声。
这种情况下,刘继隆继续沉默摸着处理政务,但不多时却有内侍快步走入殿内,在西门君遂耳边耳语了几句。
西门君遂脸色骤变,目光有些为难的看向刘继隆,可刘继隆却好像身后长了眼睛那样,在西门君遂犹豫时直接开口道:“何事?”
西门君遂见刘继隆开口询问,他这才小心翼翼上前,语气小心:“陛下,太原郡王、晋昌郡王二人于两个时辰前薨逝了……”
“……”刘继隆手中毛笔停顿,墨水滴在了奏表上,他愣神片刻后才放下毛笔,声音微微发颤。
“高、高进达也薨了吗……”
高进达,这个舍弃归义军内部富贵,跟随自己前往兰州,开创河陇太平与大汉的老臣,终究也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
王式前年就已经病危过,因此对于他的薨逝,刘继隆早就有了准备,但高进达的薨逝,着实令他预料不到。
沉吟片刻,刘继隆说不定出自己是什么心情,他只是长叹过后开口道:
“追封高进达为肃王,王式为并王,以其子高述承袭晋昌郡王爵,王涉承袭太原郡王爵。”
“追谥高进达文正,王式为文成,二人以亲王礼葬之,高进达陪葬帝陵。”
“是。”西门君遂小心翼翼的应下,同时不知怎么开口安慰刘继隆。
在他看来,以刘继隆和高进达的关系,此刻他必然悲伤不堪。
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刘继隆并没有发呆太久,只是枯坐半盏茶后,便重新拿起了桌上的毛笔,继续处理起了那些枯燥繁杂的奏表。
西门君遂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自小也曾看过前唐宣宗、懿宗,论起勤政程度,二人绑在一起恐怕都不及刘继隆。
若是二人如此勤政,恐怕大唐也不至于被取代。
想到这里,西门君遂连忙将这个危险的想法清空,后退等待刘继隆吩咐。
刘继隆侧目看向他,看他站着,不知道想到了什么,随即对他说道:
“你去金台下面坐着吧,不用一直站着。”
这话很直白,令西门君遂不知道怎么回应,愣了半晌后连忙回礼,随后走下了金台,在金台旁边坐着休息了起来。
尽管对于他来说,每日站几个时辰已经成为习惯,但眼下能坐着,他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放松。
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个好人,但似乎跟着刘继隆久了,自己的秉性都改变了。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变化的这么大,只是看到埋头理政的刘继隆时,他心里便渐渐有了答案。
在他沉思的同时,返回东宫的刘烈也看到了围在旗牌与鱼符四周的郭崇韬等人。
“旗牌鱼符已经到手,北衙六军三万兵马,足够庇护六千官吏对诸道京察。”
“京察这把火,也是时候该彻底烧起来了。”
刘烈开口走入殿内,郭崇韬几人听到声音后,纷纷转身朝着他行礼作揖,而他则是示意不用行礼。
在他话音落下后,严可求也点头道:“如今兵马官吏都齐全,确实该动手了。”
郭崇韬、赵光逢闻言点了点头,刘烈听后便开口道:“诸道之中,最难查办的是东畿和陇右。”
“陇右由孤亲自前往,孤会在办好后返回东畿,再前往河北。”
“关内道便交由卢先生,河东道则交由严先生,河北道和东畿道便辛苦赵先生和郭先生了。”
刘烈已经摸清楚了自己麾下这四位先生的性格,尽管众人都知道京察天下是惹火烧身,但陇西的火却不是一般人敢蹚的。
陇右还得他亲自前去处理,其次便是协助郭崇韬收拾东畿的勋臣官吏,最后才是河北。
按理来说,河北不用他去,但他记得自家阿耶说过,希望自己去大宁和辽东走一遭。
大宁和辽东如今百姓不多,所以被放在河北道里一块京察,他也可以借机去看看大宁和辽东的情况。
“殿下英明……”
三人对这安排十分满意,刘烈见状便点头道:“既是如此,那便等今年春闺结束后开始!”
“是!!”
随着京察诸道的事情定下,刘烈便与严可求等人忙碌了起来。
与此同时,距离此地数千里之外的安南地界,当屯田折冲府的屯兵在不断向南砍伐树木,开荒种地的时候。
在海滩捡海味的孩童们也依稀听到了号角声,不由得抬头张望。
“哪来的号角声?”
数十名孩童疑惑在海滩上寻找,最终是一个干瘦的孩童看到了海上的黑点。
“看!快看海上有船!”
“船?!”
所有孩童纷纷看向了海上,只见海上果然有黑点在移动,因此他们纷纷开始朝着黑点招起了手。
“喂!!”
孩童们在不断招手,而远处的黑点也在他们招手中不断变大,直到一艘船的轮廓出现在众人视线里。
海滩上的动静吸引了正在开荒的屯兵们,他们纷纷手持兵器来到了海滩上,生怕出现的是海盗,而非商船。
在他们的担心注视中,那艘船只渐渐清晰,而船只上的旌旗也在海风吹动下猎猎作响。
旌旗上的“大汉”二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屯兵也纷纷惊讶,没想到这么偏远的地方还有朝廷的海船。
“回来了……某终于回来了……”
“喂!!”
在海船旌旗闯入屯兵眼中的时候,屯兵村落内的“大汉”旌旗也闯入了甲板上的众人眼底。
此时此刻,身穿破烂战袄的上百名水兵跑到了船首处,看着海滩上的那群人与村落中的旌旗,忍不住的大声呼喊了起来。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昔年被派探索东洋的舰队,时隔四年终于返回了大汉的疆土……
(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