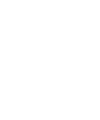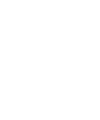红楼兵圣 - 第1章 大胜
第378章 天变
“呜呜呜~”
北风狂啸。
一夜之间,归化城变成了一座冰堡。
月余前各家商队已陆续撤回关内,带走了大量的人口,城里的商铺哪怕没有生意也需要留人,留下的几名伙计在屋里烤火,盆子里从大同运来的煤块烧的正旺。
“阿祖,看什么呢。”
伙计好奇问道。
窗口有个带着毡帽的汉子看着天,已经看了好一会,回过头皱起眉头,用着蹩脚的大周官话,“冰,不下雪,明年,大旱。”
“啊?”
年轻的伙计不可思议,随后嘲讽道,“你还能看懂天象。”
那汉子不以为然,挤到同伴里一起烤火,“这是祖辈留下的经验,一代代人都是这么讲的。”
“老一辈的人都有经验,不少人看得懂天象,你以为呢。”年长的管事说道,年轻的伙计恍然大悟,不过丢到一边,他又不种地,那年长的管事面色忧郁,“阿达,我们应该去告诉张灿将军,好人帅府早有准备。”
那汉子点了点头。
商队越来越多,归化城的贸易非常繁荣,城内常驻的就有百多家商号。
光卖杂货的就有三四十家,皮货、盐业,茶油少一些,只有十余家,但都是大商行,还有鞋庄、帽店、以及专营只对牧户售卖的鸟铳和各类刀具店。
收购的,运输的,保管的,售卖的,铺子里的,铺子外的.
归化城里为商行干活的伙计,大大小小一两万人,绝大多数来自外地,因为本地无法提供这么多劳动力,但是也从本地招募了几千人。
阿达离开了部落,加入了商队,日子与以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也没有头人打骂自己。
阿达最怕被打。
最不怕干活。
商队吃饭还管饱,每个月还有工钱,阿达想像头人一样娶个媳妇,最好能娶关内的婆姨,那才叫女人,不过还要攒几年钱才好。
不久。
越来越多的消息送入到节帅府。
“还让不让人活了。”
本就为粮食军饷忙碌了整年,刚把家小从辽东接来,打算过个好年的曾直,很快就沉着脸回到节度府,哪怕面对节帅也板着脸,一副生人勿进的可怕气息。
开春操演,初夏立威,入秋扫荡。
入秋扫荡的军队回营,三军除了各有一营始终保持全副武装之外,开始轮流放假,全军保留一半在营状态。
到了年关,节帅府都空了大半,只有少数几个留守坐班的。
空荡荡的节帅府,曾直抱怨的声音特别大。
王信倒是没有意外之色,只是脸色同样变得严肃。
虽然历史绕了一个弯,连海外都发生了变化,离大周越远,受到的影响越小,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的商人和武装势力依然出现在东南。
双方先后都与东南大周海上势力发生冲突,连粤海将军都有参与。
甚至云南安南郡王战败底兀刺国,背后也有西班牙的影子,大多变化不大。
离中国越近则不同,越近的国家,受到历史变化的影响也就很大,比如日本仍然促处于战国时期,所以没有发生入侵朝鲜的事情。
包括万历时空的三大征,本时空因为郡王实封的变化,太上皇还是皇帝的时期也都没有发生。
实封的郡王虽然对中央朝廷有大的威胁,但也对地方的统治更为深厚。
比如辽东,蛮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大周官方势力的掌控,东平郡王有小动作,可他仍然代表大周。
不过气候却不会受到影响,该来的还是来了。
小冰河时期大名鼎鼎,王信记得看到过一篇官方数据,来自中国天气网的五百年大数据,万历六年大旱、崇祯七年大旱、乾隆五年旱灾,以及光绪三年大旱。
其中最严重的要数崇祯七年大旱。
因为崇祯朝之前数十年灾害就连绵不断,国力见底。
等到了崇祯七年大旱更属于全国大旱。
波及南北二十三个省份的苦旱导致赤地千里,江河断流,泉井涸竭,禾苗干枯,颗粒无收,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简而言之,再多的银子也没有用,因为全国都不产粮食。
这也是崇祯朝收的税赋远胜之前,结果军队士兵连饭都吃不饱。
以大明的体量面临全国缺粮的灾难,这个灾难只怕全世界都供应不起。
无解的灾难。
“扩张吧。”
王信只能想到一个办法。
曾直等人愣住了,他们有些傻眼,“是不是太过了?”曾直连忙劝道,“灾害又不是一年两年,打我记事起,咱们大周的灾害就没有停过,熬个一二年,苦一苦熬两三年,老天爷总会给人喘口气。”
眼前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面临什么。
遍布全国整整七年的大旱。
连江河都断流了,更何况湖泊,打井自救也没用,因为井水也枯竭,跑山上也救不了命,因为泉水也枯竭了。
赤地千里,多么可怕的末世景象。
怎么重视也不为过。
“往关外什么地方扩?”严中正倒是猜到王信的打算,如果在关外的话,只要控制得当,影响大概会小一些。
“哪里有好的土地,就往什么方向扩。”王信知道会有很多麻烦,但是必须这么做,“关外的灾害必然发生,牧户们的草场必然遭受影响,没有别的法子,唯独获得更多的草场。”
严中正猜到了,心情沉重。
节帅的态度有些太过紧张,但是草原的灾害也的确在发生。
灾害下的扩张,不会获得更多的牛羊,只为了保住现在的牛羊规模,而军队却需要承受更大的代价,并不是畏惧代价,可如果付出代价,能换来更多的牛羊,心里也好受些。
“没钱。”
曾直拍了拍手,果断的说道。
不久后。
许多商家收到了节帅府的请帖。
“动静闹得太大了。”
这个年过得不安逸,匆匆赶回衙门的曾直,被一个个商行拜访,想要了解节帅府要做什么事,看到商人们的动静,曾直心里有些担心。
“的确有点大。”严中正也点了点头。
只怕很快会惊动御史。
“知府来了。”
薛蝌小跑进来,“去见了节帅。”
知府怎么来节度府了?难道是因为商人们的动静,曾直与严中正互相看了一眼,曾直提议:“去看看。”
严中正同意。
此时。
知府韩彬已经坐在大厅下方左边第一个椅子,他是第一次来,进大厅后看了看厅里的陈设,没想到会如此节俭,忍不住又看了眼眼前才三十几岁的节度使。
他的下首坐着翟文。
翟文终于熬出头,虽然没有升品级,但是从观察使调为大同同知,仍然是正五品的文官,但已经是知府的副职,分管大同盐、粮、水利等事务。
翟文笑道:“节帅,我们不请自来,有事相求啊。”
“何事?”
王信了然,难怪韩彬带着翟文。
翟文知道自己的作用,态度端正,恭敬道:“大同府衙已经半年没有发俸禄了,下面官吏已经揭不开锅,咱们也实在没有办法,还请节帅伸伸手帮衬帮衬。”
原来如此。
王信又好笑,心里危机感也大增。
朝廷下拨给大同军镇的军饷粮饷越来越晚,虽然张吉甫没有少自己的,但连大同知府府衙都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可见他难成了什么样子。
“没钱。”王信直接拒绝。
开玩笑呢。
他恨不得拼命攒钱,怎么会把钱拿出去借给别人,如今的局势,只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虽然能获得知府的好感,可知府的好感值几个钱?
翟文没有意外,看了眼身旁的韩彬。
韩彬坐不住,终于开口,“节帅,你我同朝为官,虽文武分途,可大伙为了朝廷办事,更为了天下苍生,节帅向来名声极好,此次如何见死不救呢。”
没想到官员也夸起自己了。
如果是平常的话,他当然会卖面子,可他明明清楚未来有多凶险,怎么还会答应呢。
王信叹了口气,客气道:“帅府五六万军士,养活十余万口,府台大人比谁都清楚,并不是本镇不近人情,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凡有多的,怎敢拒绝府台大人。”
王信把话说到如此地步,翟文主动起身,韩彬也无奈离开。
等两人离开,严中正与曾直赶来询问。
搞清楚后,两人面色负责。
“没想到会这样。”曾直不可思议。
王信严肃起来,希望曾直能重视,声音沉重,“张吉甫做事向来有分寸,不会把事情做绝,如不是确实没有办法,绝不会让大同知府难到这般地步,可见去年各地上交的税赋超乎了他的意料。”
一千六百万两银子是大致的税赋,常年维持在这个水平。
或多或少。
最高的几年到了一千八九百万两,东南倭患那几年回落到一千四五百万两,张吉甫入京后,慢慢恢复到一千七百万两,明明税赋恢复,各地却难以为继。
因为物价上涨。
那么今年的税赋收了多少呢?一千五百万两有没有?
或者比一千五百万两更少。
“广积粮吧。”
王信认真交代,“未来的数年,节帅府只有一个目标,广积粮,想尽办法的积粮。”
曾直不在犹豫。
越来越多的商户回到大同,准备去关外贸易,收到名帖的商家更多了,约定在四月份,节度府消息有控制的紧,竟然谁都不知道节帅府要做什么。
不过如此大费周章,大家都猜到会有大事发生,谁也不敢错过机会。
广积粮是办法。
但是大周粮食产量有定数,在极度欠缺的情形下,大同军镇积蓄粮食越多,百姓们吃的就更少。
换成有些人巴不得。
但是王信认为这是不对的。
一个势力如果做不对的事情,那么这个势力的属性就会有问题,属性有问题,就无法成为那双在市场上公平公正公开的大手,更加不能公平公正公开的调节。
所以身为一方势力的掌舵者,王信必须要做对的事情,养成一股正确的风气。
所以该怎么积粮呢。
四月。
一家家商号东家,或者大掌柜齐聚,薛家薛岩和张德辉都来了。
“以商行为主,可以成立开垦商号,负责草原上开垦耕地和放牧牧地,可以申请军队保护,协助商号的安全,以及消除威胁。”
王信给了一个价。
最小的单位为队。
最大的单位为小营。
武器装备马匹是现成的,但是商行需要支付租金。
装备和马匹的租金,军队与士兵一人一半,同时商行需要支付士兵报酬,每人每月三两银子,同时提供吃喝,如果士兵受伤或者战死,商行需要赔付抚恤。
马匹受伤和死亡,商行需要以市场价折算后补偿。
平均下来。
每名士兵的成本在十二两银子一个月。
雇佣的规模越大,使用的期限越长,成本会越低,前提是不超过小营的规模,也就是四百五十人,超过了这个数量,后勤的难度直线上升,成本会更高。
性价比最高的是哨。
一哨九十人,租用三年,一般情况下,成本可以做到五两银子每个月,一年五千四百两。
九十名职业骑兵,全副武装。
哪怕在原来的胡人部落里,也算不可小觑的势力,可以荡平很多小台吉。
真要是有难缠的敌人,大不了咬咬牙,钱请小营三个月。
土地永远是值钱的。
因为土地有限,而土地无论过了多久,永远还是土地,房子的核心是土地,而不是房子,房子并不是永恒的资产,土地才是。
哪家不羡慕聚众昌?
别看聚众昌抱怨节帅府管的严,可账目是明的,一笔长期的持续性收益的利益,没有人不动心。
成本依然转嫁给商人。
军队打下更多的土地。
商人不怕投资。
商人在意的是未来。
只要未来预期足够大,投入多少本金都不妨碍商人浓浓升起的欲望。
这就是商业。
在些许试探,小队哨队的聘请,半年之后,十八家商号联合请了一支大同小营,向大宁放心开阔,那边有一片富庶的土地,原本是北静郡王的藩地。
商号的管事带着伙计们圈地。
沿着水源一带。
插上商队的旗号,在土地下埋入商号在帅府登记后颁发的牌子。牌子分为三块,帅府一块,商队一块,地下埋藏一块,然后在帅府的舆图上,这块土地就属于商号的了。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买卖,商人们高兴疯了。
麦子熟了五千次,商人圈地第一次。
“谁说节帅对我们提防的?谁说节帅对我们过河拆桥?”有商人骂道:“说以后敢在我面前说节帅的坏话,我第一个不饶他。”
当着伙计管事们的面,商人拍着王信的马匹。
不远处的哨官高兴的点了点头。
第二日一早,精神抖擞的带着兄弟们骑上马,往周边扫荡,消除隐患。
商人越发高兴。
高价钱请来的军队,当然希望对方努力干活,最好马不停蹄,日夜不休的消灭周边隐患,他才好更快的开垦土地,早一点出产,早一点回本。
带着商队和军队,睁开眼的每一天,人吃马嚼都是他家的钱,心疼的不得了。
有人欢喜有人愁。
大半年下来。
有的商人成功获得了几万上十万亩的牧地,有的商人却血本无归,承担不起高额的费用,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风险,以至于破产。
获得了土地只是第一步,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开发。
仿佛是个无底洞似的,把商人们的钱从地底下挖出来,投入到关外。
无数的人分到了钱。
军人伙计马夫车夫兽医大夫带着丰厚的工钱回家,然后在集市里买东西出去。
“王信在干什么?”
李源被升为兵部尚书,知道张吉甫转变态度开始拉拢自己,李源也开始支持张吉甫,收到密云军队送来的军情,皱起眉头前往内阁。
张吉甫不耐烦的敲了敲桌子。
他给王信的还不够多嘛,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添麻烦。
(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