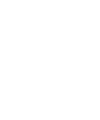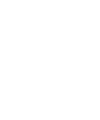寒门国舅 - 第696章 学问
第696章 学问
偏头关前。
李孜省、覃昌一行,带着大批的军械和布帛等物资,总算是辗转到来,而此时有关李孜省上任山西巡抚的圣旨还没送达。
偏关守军可不想迎这么一群人进入关口。
正如朝中很多人所担心的那样,地方军务涉及到军队统属以及军令传达,而李孜省带兵进驻偏关这件事属于理不直事不正,会牵扯到很多权力上的冲突。
因为接洽没完成,当晚李孜省麾下人马,只能暂时驻扎在关口以外。
而偏关城塞内则派出一名书吏,前来跟李孜省一行进行接洽,着重提到了粮食供给问题……
李孜省这一战打得很热闹,但因为他麾下行军带的都是干粮,自给自足都很困难,加上他又征调了王方的人马,人家大同兵可不想自备干粮来打仗,所以李孜省得供应这群人吃喝。
再加上战时损耗比较大,李孜省这边缺少军粮供给,只能进关城采购补充。
但显然偏关不想承担这笔开销。
你是来送军需物资的,莫名其妙打了一场仗,还让我们供应你吃喝?我们自己很多士兵都苦熬着呢。
“总兵官何在?为何不来见咱家?”
覃昌拿出身为司礼监太监的威严,朝着那书吏一通喝斥。
李孜省低声提醒:“山西总兵官并不常设,如今偏关内并无总兵官。”
覃昌一怔,随即想到李孜省之前就是大明朝无冕的吏部尚书,显然其对西北官场架构上的事比他了解得更多,而他身为内相,很多事无法整明白。
这也是当初怀恩被放逐后,为何成化帝会很快疏远覃昌的原因。
因为覃昌除了能力远不能与怀恩相比外,本身也不够勤奋,遇到事情不求甚解,照理说天下官员他心中应该都有一本账,当皇帝提到哪个人时他应该第一时间介绍情况,但实际上他却是一问三不知,每每都要回去查阅资料后次日才能给出答案。
随后覃昌颐指气使,对着来人一通呼喝,才把人打发回去准备。
……
……
人走后,覃昌这才想起来要问问李孜省有关偏关的事。
“李尚书,你之前从未曾踏足过偏头关,但好像对这里的情况很了解?”
覃昌也觉得不可思议。
以前只觉得李孜省是个一手遮天的恶棍,只知道卖官鬻爵。
经过这一趟下来,覃昌发现,自己对李孜省的认知远远不够。
李孜省道:“就说山西总兵吧,自从成化十七年王信卸任后,朝廷就一直未再设。这也是因当初王越打了几场胜仗后,鞑靼人久不敢来犯所致。”
覃昌道:“先前你就说过,山西巡抚人在太原,总兵府却设在偏关,如今适逢总兵官出缺,那谁来照应咱?总不会让咱在这里自给自足,等开春后自己找人种粮食吧?”
“呵呵。”
李孜省莞尔一笑,道,“战事随时都会开启,覃公公言笑了。”
覃昌显得有几分不满,道:“你是都御史,领兵之事由你负责,总不能靠咱家在西北刷脸……你赶紧给想个对策!要不,咱家这就向京师求援,打仗需要足够的粮草方才有机会取胜!”
……
……
丫角山。
保国公朱永亲率京营人马,经过长途奔袭赶路后,终于进入偏头关地界。
朱永手持望远镜,站在高处看了许久,此时日落时分,沿途城关不见人迹,他心中多了几分担忧。
远处一骑踏着尘烟而来,却是他的儿子朱晖纵马赶到。
“父亲。”
朱晖跳下马来。
此时的朱晖年已过四旬,身体看上去有些富态,好像还没有他那年过六旬的老父亲朱永来得壮实。
朱永见儿子下马走到自己身边时,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不由皱眉道:“这两年你疏于锻炼,莫不是连马背上的功夫都退步了?”
朱晖面色有些尴尬,却赶紧将自己查到的情况向老父亲汇报:“……据说那位李道长就是带兵从这里折道往北,出关口跟鞑靼人交战的……他们既没有等咱,也没有跟咱打招呼,直接导致咱们与战功交错而过……他们的人马现在应该已经开进了偏头关。”
朱永把马缰折迭了一下,问道:“附近可有鞑子活动的迹象?”
作为明朝成化年间,靠军功晋封公爵的新贵,朱永并没有一般勋臣那种得过且过的保守心态,他在治军上非常有经验,往往能通过表象看到实质。
大明的勋臣有个通病,那就是进取心普遍不强,朱永也只是比那些人强一点。
朱晖道:“这附近的人马,都奉调往偏头关方向开拔,留守的并不多,据说这是山西地方上的安排,并不是出自李道长的指示。”
朱永点头道:“李道长虽为都御史,但并不管辖山西地面的军政事务,战事爆发后,把一些防备不足的土关、土堡的人马调回大的城塞,本无可厚非,但这次取得一场大捷后还要这么急着调兵遣将,倒像是故意出纰漏,给人好看。”
“父亲,您的意思是……?”
朱晖面带不解。
打仗的事,朱晖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多年,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
战场之外的事情,朱晖则所悉不多。
要是换作一般人,肯定懒得跟朱晖多做解释。
但眼前人毕竟是朱晖的老父亲。
朱永生怕自己得来的公爵爵位,到儿子这一代传不下去,毕竟当初领导他的汪直、王越二人已倒台,他朱永算是侥幸逃过罪责,保国公这一脉得来的公爵传承,也多被朝臣认为理不直气不壮。
你靠相对太平年景的几场战事获胜,就获得世袭的公爵爵位,让那些开国和靖难公侯怎么想?
朱永道:“鞑靼来犯,本地人马本不能撤,也不敢撤,可是如今陛下派李道长到偏关治军,沿途征调兵马,你说山西将官还不趁机把自家人马都调走,如此一来,就算朝廷问责,也能把责任全都推到李道长身上……”
朱晖似乎还是没弄明白,问道:“他们会假借李道长调兵的名义行事?”
朱永摇头道:“李道长是否调兵,事后一查便知。他们不过是想创造一种军令阻塞,且上下失调的现象。越是混乱的时候,越有人喜欢浑水摸鱼。”
“哦。”
朱晖似懂非懂,稍微琢磨了一下,又问,“那咱们现在该如何做?是加紧往偏关去,还是说……驻扎在此,等鞑靼人前来?”
朱永道:“你确定鞑靼人敢来吗?”
朱晖无奈道:“这如何能确定?”
朱永叹道:“我们虽名义上听从李道长调遣,但毕竟我乃新任宁夏总兵官,在偏关之地治军,本就于法理不合。
“说起来,难道朝中就没人想到这一节?该赶紧把李道长安排到偏关合适的位置上,免得从上到下都推脱,不做实事,或将直接导致此番对鞑靼战事先胜后败,辱没大明朝廷的威风。”
“父亲,您的意思是说,朝廷应该把李道长安排在本地就职?他不是……还得把军服和布料等军需物品,送到西北各军镇么?”
朱晖问道。
“那些都是借口。”
朱永道,“陛下初登大宝,派心腹李道长往西北来,难道只是为了送点儿东西?要只是押送物资,派谁来不行?这位李道长也是能人,先皇时就权倾朝野,如今仍旧气势不倒,光看他能带兵抵御外辱,就非一般人能及。”
朱晖摇头道:“但在孩儿看来,那李道长不过是会攀附而已,否则,他上哪儿得来军功?”
朱永往儿子身上瞅一眼,道:“懂得见风使舵,也懂得攀附谁对自己最有利,看似急功近利,其实暗藏玄机。你能学到他一成本事,就足以在朝中安身立命。可惜啊……”
虽然父子俩没有再把话说太透彻。
可也让朱永把此事放到心里去了。
他在想,原来想在朝中安身立命,主要是靠巴结好重要的人?那这谁不会?看来我这位父亲做人做官的学问,也不过如此。
(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